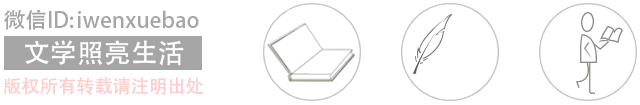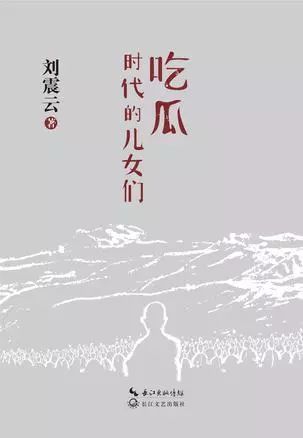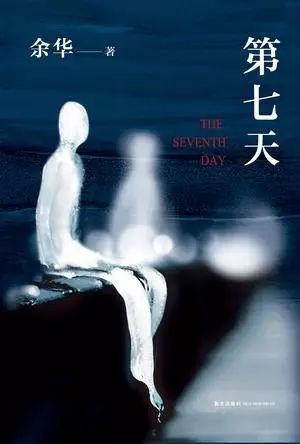文学面对现实应避免随波逐流——由《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说开去 | 新批评
刘震云笔下的
“现实——历史——现实”
继《我不是潘金莲》之后,暌违五年之久,刘震云又推出了以“反腐”为题材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把四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串联进一部长篇小说之中。观察刘震云的创作可以看出,从成名时期的“新写实”小说,到“故乡系列”等历史题材的作品,再到如今的“上访”和“反腐”,他显然走了一条“现实——历史——现实”的取材路线。但“新写实”的路径是普通人的日常琐事,而归返之后的现实则大多是“现实事件”。只不过,在这些作品触及“现实事件”的时候,因为现实的“事件化”,让刘震云善于说故事、打幽默的叙述方式遭遇了某种瓶颈,肆意挥洒的才华被禁锢在“现实事件”的真实性上,一俟进入小说文本,这种处处被捆绑的“事件化”的“现实感”,让人不禁感叹起文学正面触碰现实带来的阅读束缚感。
妇女列传之牛小丽
如果要给《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寻找一个纽带的话,那么它无疑是四个陌生人物中的一个——牛小丽。刘震云为了让已经被“事件化”了的“反腐”事实不至于生硬地被移植在小说中,费尽心机地勾连了一个文本叙事的“结构网络”,从而把整个小说文本编织成一个以牛小丽为核心的“叙述蜘蛛网”。在具体的讲述过程中,再以提纲挈领的方式,拎出这个女人,把整个反腐故事中形形色色的“群吏形象”一网打尽,让一群“吃瓜群众”傻乐呵呵地,一边吃着西瓜,一边看着无关痛痒的腐败“荒唐”事件,还不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品头论足,消费着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因此,抓住牛小丽,也就能居于这部小说的“风暴眼”,一切外在的“反腐”大戏,不管如何轰轰烈烈,紧张刺激,都成了如同屏幕上展演的虚幻影像,让读者真正成为“吃瓜群众”。
从精神谱系上给牛小丽找到她的归属,这个谱系便是刘震云笔下塑造的一系列中国大地上的普通妇女形象。与牛小丽最具亲缘关系的自然还是《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她们几乎是孪生姐妹——执拗又泼辣大胆,天不怕地不怕,遇事有主见,且是家庭中的主心骨。小说的开端处,刘震云上来展现的仍旧是“事件化”了的生活真实:拐卖妇女与假婚行骗。牛小丽即将出嫁,操劳着给窝囊的哥哥买一个外地老婆,却不成想被这个叫做宋彩霞的妇女给骗了。为了寻回买女人花费的15万元,牛小丽执拗地前往西南某省,追踪宋彩霞的下落,又被介绍人给骗了,把她一个人扔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最终,把宋彩霞留下的假的家庭地址上的整个县城和下属的十二个乡镇全部跑遍了,却毫无结果,还在寻找的路上差点被司机半路劫色。万般无奈之下,被一个从事色情业的女人骗走。
但作为一个良家妇女的牛小丽,前后行事的逻辑实在“矛盾百出”——她既可以千里迢迢,不妥协地寻找被骗走的钱财,居然也能那么顺理成章地就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尽管她有自己的无奈之处,但绝不至于到了山穷水尽以至于要出卖身体的地步……这种种矛盾之处,也彰显出了刘震云在涉及对“事件化”的生活现实进行文学化表达的时候,顾此失彼的一面,毕竟,牛小丽只不过是他临时征用来暴露反腐大案的一个可怜的乡下妇女罢了,至于她的内心、性格、背景等等,则完全被忽略了。然而可惜的是,整个《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写得最好的一个人物形象,恰恰又是牛小丽。刘震云要给“吃瓜群众”展示的“荒唐”腐败案件,也以“荒唐”的文学效果,让“吃瓜群众”不忍卒读。
群吏列传之李安邦与杨开拓
围绕着牛小丽团团转的,是一群“贪官污吏”,既有省长、市长、县长,也有县上某个局处的小领导、银行行长。和历代正史书籍中的“酷吏”、“廉吏”等不同的是,他们具有了“现代性”的思维逻辑和行事风格。在刘震云的小说系列中,他们的前辈就是《我不是潘金莲》中“人人自危又人人自保”的懒政怠政者——为了尽量不给自己惹麻烦,能推则推,能躲则躲,让一个芝麻变成了一个西瓜,让一只蚂蚁变成了一头大象。
李安邦作为一个省长,从秘密渠道获知消息,自己有望成为省委书记,便开始了前后的“打点”。但不巧的是,各种倒霉事都聚集过来:他试图讨好翻脸的朋友,使其不要背后说怀话,还算是官场中常见的事情;他的儿子出车祸,但要摆平的不是车祸本身,而是车祸中死去的一个女人;他的妻子直接越过他,收受商人送来的巨额资金,还没有政治头脑地外四处张扬;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又接着被查出贪腐问题,担心这个胆小怕事的部下透露出自己的问题。所有的焦虑集中起来,让他孤立无援中只能找到商人赵平凡。赵平凡一点都不平凡,他人脉关系极广,在政界和商界叱咤风云,表面金盆洗手四处做慈善捐款,背地里却仍旧做着各种勾当。正是他出的主意,带着李安邦找到了神秘兮兮的道人一宗,于是才有了与牛小丽牵扯到一起缘由。
更具“事件化”的故事属于杨开拓,却也彰显刘震云应对现实的无力感,最为集中的一个人物形象。在小说中,抖开整个贪腐网络的人,正是荒诞漩涡中的杨开拓。他参加外甥的婚礼之时,发生了一件“新闻事件”——运送烟花爆竹的货车爆炸,将“彩虹三桥”炸断。奔赴现场的他面对混乱的现场,回答市长问话的时候竟然“傻笑着点了点头”,最终这张傻笑的照片在网络上引起了全民公愤,让他获得了“微笑哥”的网络称号。不仅如此,人们还将他戴着的手表单独截图出来,又搜罗出他在其它场合所佩戴的手表图片,指证了他的贪污,让他又获得了“表哥”的网络绰号。最终杨开拓被“双开”,隔离审查,牵扯出了牛小丽的卖身,又顺藤摸瓜地将十二个与牛小丽发生关系的官员一网打尽。
至此,刘震云用了一个偶然的爆竹炸断桥梁作为收网的绳子,把各类“反腐事件”、“新闻事件”和“网络事件”,拼凑到一起,以牛小丽作为中心,将之串联起来,构筑了一部全新的小说。人们不禁要追问,倘若如此简单地抄录这些“事件化”了的真实故事,就能成为一部小说,那么作家的工作也未免太过于简单了。人们不得不怀疑,刘震云到底是在将“当下历史化”,还是在借助“事件化”的存在,将自己及其创作“历史化”呢?
荒唐作为“扣子”
为了让这部小说摆脱“抄袭”网络和现实的嫌疑,刘震云煞费苦心——他找来了“吃瓜群众”作为掩护,言下之意是要以这样一个荒唐的“反腐”故事,来彰显当下社会大众的生活状态,却一不小心滑入了“事件化”的现实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他又找来牛小丽作为结构的核心点,把不相干的几个人串连在一起,来凸显当下时代网络的神奇功能,以及网络对大众生活的本质性改变,以此来用“吃瓜时代”命名这一段历史。为了突出“吃瓜时代”的特征,刘震云又征用了“女明星出轨人妖”以及微信监管的“删除功能”等,试图把这个电子时代的“无关联的关联性”,在小说中以“哲理化”的方式给表达出来。但叙述至此,即便不读原著的人也能感觉出来,相比较于为“吃瓜时代”把脉,“移植网络事件”更像是这部作品的核心要件,它所占的比重、它所彰显出来的时代特征……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不像是为“电子时代”立传。
为了圆整个小说的故事,刘震云找了整个故事叙述的“扣子”,即荒唐。在小说行将结尾的地方,刘震云交代道:“啥叫荒唐?事情荒唐不叫荒唐,把荒唐当工作做才叫荒唐;把荒唐当工作做也不叫荒唐,联防队员把‘钓鱼执法’的钱拿回家,他老婆又拿这钱去过日子才叫荒唐。你也荒唐,我也荒唐,大家共同靠荒唐过日子,荒唐可不就成了正常?”“吃瓜群众”看的事情是荒唐,而官员们把荒唐当作工作做也成了荒唐,荒唐成为日常,便是“吃瓜时代”的典型特征。
刘震云或许忘了,靠着“荒唐”的魔力无法解除附着于这部小说之上的平庸与乏味,正如让一个“倔强”的农村妇女拯救一群懒政怠政的官员们一样。牛小丽作为整个叙事网络的核心,串联起了整个“网络事件”的线索,看似毫无拼贴痕迹,但并未摆脱对网络事件的“移植和拼贴”。加上牛小丽行事逻辑前后的矛盾、李安邦与杨开拓的简单化等,使得四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仍旧呈现出一种撕裂感,一种硬性拼凑的痕迹。
近年来,先有余华对现实“正面强攻”的《第七天》,接着有关仁山探索土地流转的《麦河》,再有徐则臣关注雾霾的《王城如海》等,他们都试图对现实发声,介入现实社会之中,从而彰显文学的力量。但对于他们而言,触碰现实的无力感在小说中就表现为拼凑“事件化”的现实、大段议论代替小说叙述、截取网络故事作为小说素材、照搬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人们不禁追问,追逐“社会热点”,造成“爆红效应”,却唯独不顾及文学本身的规约,让文学径直成为“网络事件的作家版”,这是否会对当代文学造成致命的伤害?或许,学界和作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反思依然远远不够。
2018文学周历已在我们微店中上架,
订阅2018《文学报》还有周边赠送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