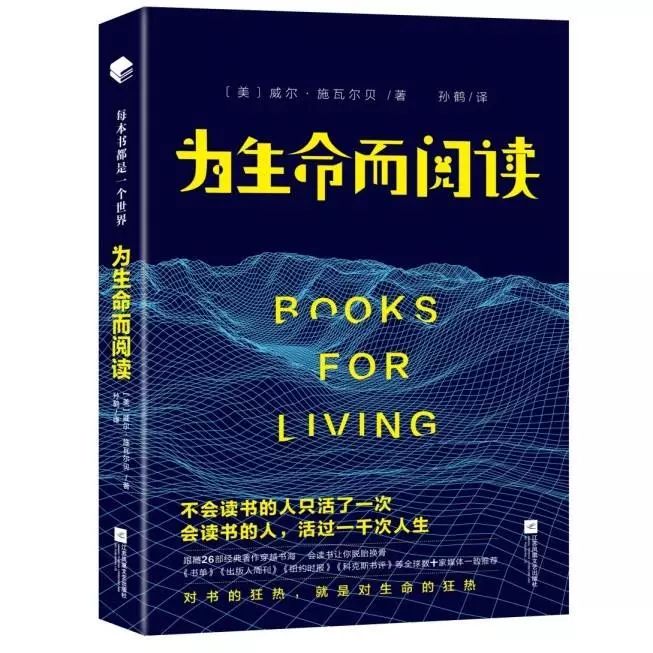林语堂:最精致的生活,一定是素与简(4)

林语堂于1895年出生在中国,在家里八个孩子里排行老五。
他的父亲小时候没有受过教育,不过在青年时期自学了读写,并最终在家乡福建省龙溪县建了座小教堂,并担任牧师。
很小的时候,林语堂就跳上父亲的讲道坛在集会上演讲。从那时起,他就展现出了对语言的热爱。
林语堂在中国的一所西式大学里学习神学,不过很快他就因为无法接触伟大的中国本土文化而感到困扰。从那时起,他开始学习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道教和佛教。

林语堂上大学时,他挚爱的一个姐妹由于父亲反对没能上大学,只能结婚,并在怀胎八个月时死于瘟疫。从那时起,林语堂积极主张为女性争取高等教育机会,同时决定穷其一生争取社会公平。
1919年,林语堂来到了哈佛大学学习,不过很快就因无法负担学费而退学。
他来到欧洲,先在法国打工,后来在德国继续接受教育并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用德语写就了关于中国语言学的学术论文。
他于1923年回到中国任教,其间由于国民政府的限制暂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在上海继续教书,并开始频繁地为他创办的杂志写稿,开辟了多个批评国民政府的专栏。
1933年,正是在上海,他遇到了专栏的忠实读者珀尔·巴克。
1935年,在他的第一本书《吾国与吾民》获得成功后(《纽约时报》后来评价这本书“如同在西方世界投下了炸弹”),林语堂迁往纽约,并在那里写就了一系列作品,包括《生活的艺术》和1943年出版的《啼笑皆非》,这本书对美国在国内外推行的种族政策进行了抨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林语堂回到中国进行报道,这次他称赞了国民政府。不过在这一时期,他醉心于研究中文打字机。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与英文只有二十六个字母不同,中文有成千上万个独立的汉字。
林语堂将他全部出书所得都投入其中,但是无数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他没能设计出可以大批量生产且价格可以为市场接受的模型。尽管如此,他创造的概念和技术后来还是被应用于密码破译和转录机。
对中文打字机的大量投入致使林语堂和夫人在战后破产,此时他们与三个未成年的女儿生活在纽约。
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请他赴巴黎出任美术与文学主任,一家人的经济困境才得以缓解。尽管他憎恶早起上班,但此时已别无选择。
林语堂晚年经济条件转好,他再次专心于写作和学术研究。
他督办了第一部现代中英词典的编写,这项工作规模庞大。他还一度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
20世纪50年代,林语堂重返纽约并重新信奉基督教。在1966年来到台北前,他与妻子和三个女儿在纽约居住。1976年,林语堂在台北辞世,享年八十岁。
如果在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就已经感觉到了放慢脚步的迫切性,那么如果他活在现今,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不管是在《生活的艺术》的创作地美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业国家。
不过,林语堂早已指出,闲适生活一直都很难。我的这种表现不足为奇,不能仅归因于电子设备。即便把苹果手机放进口袋,什么都不做对我来说还是很难。喧嚣忙乱的生活会出现在我的脑海。
当我反复阅读《生活的艺术》后,我突然意识到它倡导的并不是行为层面的改变,比如看手机,而是关于如何看待周遭事物的根本改变。
就拿林语堂对安卧眠床的喜爱来说,躺在床上并不是一项活动,而是放慢生活脚步的方式。你可以沉思、倾听,甚至阅读。
因此我经常躺在床上读《生活的艺术》。这本书非常适合用零散时间来阅读。
每隔几页就有一些句子跳出来,我得思考消化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比如这句“我认为对于感官和情绪的教育要远比对想法的教育重要得多”。
随着我反复阅读《生活的艺术》,我愈加意识到它并非讲述闲适哲学,而是如书名所示,它诠释了生活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