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叶斯大脑(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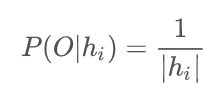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满足“都是4的幂次”假设的结果只有4,16,64三种,所以16对应的似然概率为1/3。
根据贝叶斯定理,最终对每种假设的信念便是两者的乘积,既要考虑到先验假设,也要考虑到似然概率,相乘的结果显示在图中横坐标为“post"的右侧。对于”都是偶数“这样的假设,尽管先验概率比较大,但因为1到100间的偶数太多,出现16的概率仅1/50,如果恰恰出现了,我们会觉得是“惊人的巧合”,而不太会相信它是真的。这对应着贝叶斯版的Occam剃刀,在机器学习中,它化身为正则化项以防止模型过拟合。
这样,我们就有了知道数字16后各模型的后验概率P(h_i|O),从中我们就可以选择概率最大的一个作为最大似然估计,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选出的模型是“都是4的幂次”。如果有更多的证据,模型便会快速收敛至真实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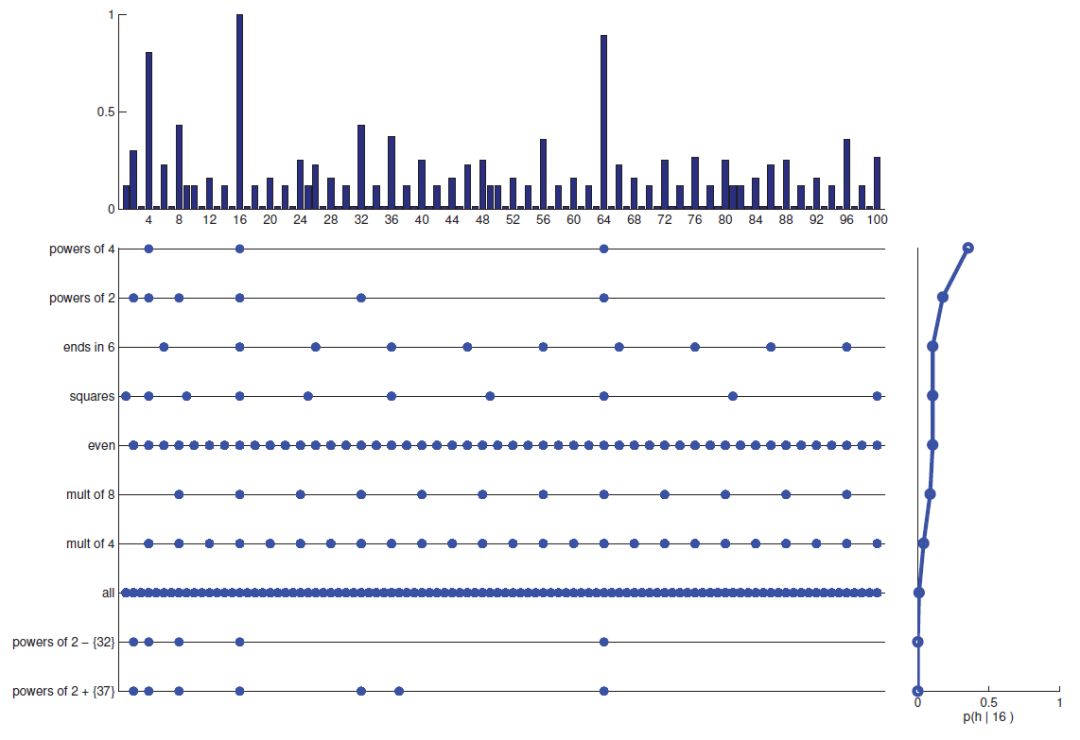
那么我们又是如何猜测下一个数字x的呢?我们已经有了每个模型的后验概率,下一个数字是x的概率就可以表示为每个模型的后验概率和相应模型出现x的概率的乘积的求和,俗称贝叶斯模型平均。表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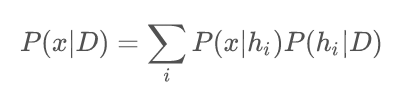
这一计算过程漂亮的反映在上图中。中间那一大块图纵轴表示各种可能假设,而每条横线表示1到100的数值区间,那么每条线上的点便表示各模型假设允许出现的数值。可以看到假设“all"的横线布满了点,因为从1到100,它每个数都可以取到。我们再看图的右边那条曲线,它表示的便是给定数值16后各模型的后验概率分布,可以看到,假设”都是4的幂次“的后验概率最大。将两者结合并叠加起来,就会得到图中上部所示的x的概率分布。可以看到,数字16,64,4的概率最大,与我们料想的非常一致。

我们再看大脑推断中用到贝叶斯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同样来自Tenenbaum[2]的论文,说的不仅仅是我们如何学习单个概念,还说明了我们是如何将概念对应到事物的不同范畴的。所谓范畴,就是对事物的分类,并且这种分类通常是有不同层次的。例如你的写字桌,它既属于写字桌这一类,也属于桌子这一类,还属于家具这一类,在范畴论中,它分别可以对应着下位范畴、基本范畴和上位范畴。

在Tenenbaum论文的例子中,当指着一张标记为fep的斑点狗图片,来猜测fep的含义时,我们既可以认为fep表示上位范畴的动物,表示基本范畴的狗,也可以是表示下位范畴的斑点狗。而我们会倾向于推断fep的意思是狗。这是由基本范畴偏差(prior)造成的,因为我们日常处理事物大多都在基本范畴,这也是为什么基本范畴的中英文单词大多非常简单且长度很短。但当给了三张斑点狗的图片,而且每张都标记为fep的时候,我们却更可能推断fep意思是斑点狗而不是所有的狗。因为直观上来讲,如果fep表示的是所有的狗,但随机抽取的三个样本都是斑点狗,那将是“惊人的巧合”。

第二个例子来自刘未鹏的《暗时间》,里面提到了一个自然语言的二义性例子。
the girl saw the boy with a telescope.
对于上面这句话,我们既可以理解为那个女孩拿着望远镜看那个男孩,也可以理解为那个女孩看到那个拿着望远镜的男孩。那么为什么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想当然的理解为第一个意思而消除歧义?从语法结构上讲,两种结构都是成立的,在这里体现为先验概率P(h)大致一样,但是P(O|h)却很不一样。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为何偏偏那个男孩拿的是一个望远镜,而不是一本书或一只苹果呢?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恰巧是望远镜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如果用第一种语义理解就不一样了,女孩通过某种东西看男孩,那么,拿的是望远镜就很显然。
在很多情况下,贝叶斯原理很好用,我们大脑也用它做很多事。但另一方面,它也是认知偏差的孵化池。
认知偏差
在《机器人叛乱》一书中,斯坦诺维奇讲到了认知心理学文献中的琳达问题:
琳达今年31岁,单身、率真、非常聪明。她的专业是哲学。作为一个学生,她格外关心歧视和社会公正问题,也曾参加过反核示威游行。请根据可能性对下面的陈述进行评价,1代表可能性最高,8代表可能性最低。
a. 琳达是一名小学老师。
b. 琳达在书店工作,上瑜伽课。
c. 琳达积极参加女权运动。
d. 琳达是一名精神病学的社工。
e. 琳达是妇女选民联盟的一员。
f. 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
g. 琳达是一名保险销售员。
h. 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积极参加女权运动。
因为选项h是选项c和f的组合,所以从概率来看,肯定比两者来得小,但是研究表明,有85%的参与者出现了“组合偏差”,他们认为选项h比f的可能性更高。
这可以看成是混淆了似然概率与后验概率的区别。本来需要计算后验概率P(h|O),却计算了似然函数P(O|h),或者说本来需要用induction的地方却错误的使用了ded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