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是不服从的最纯粹形式
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后第一部长篇小说《庶出的标志》中文版于去年八月出版。这部小说一度被当作政治小说被批评家广泛研究,同时也是纳博科夫政治色彩最浓郁的小说,尽管他本人一直拒绝承认这一点。纳博科夫将现实的见闻与经历编织进虚构的文字之中,集政治讽喻、人物肖像、文字游戏于一体,穿插对文学经典的颠覆解读。
小说的背景置于一个荒诞不经的警察国家,人们信奉埃克利斯主义,追求整齐划一的埃特盟(普通人)式生活,浑噩无知又胡作非为是国民的通性。主人公克鲁格是该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享誉海外,为了让他为新政权背书,独裁领导人巴图克百般尝试却不得法,最后挟持了克鲁格幼小的儿子,通过这一小小的“爱的杠杆”,撬动了固执的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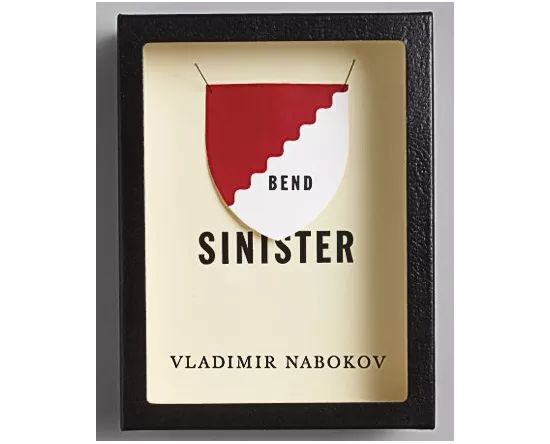
“庶出的标志”一词指的是从盾徽右上方到左下方的对角斜纹,有表示私生子的含义。纳博科夫本人曾表示,选择这个标题,是想暗示一种被折射破坏的线型轮廓,一幅镜中的扭曲图像,一次生活的错误转向,一个怪诞邪恶的世界。
好奇心是不服从的最纯粹形式
文|萧轶
原发于|单读
- 声明:刊发已获授权,转载先请私信联系 -
谈论纳博科夫是种危险的愉悦,每一个读过纳博科夫的人都再熟悉不过了。
危险在于纳博科夫总是不忘时刻揶揄评论家们,无论是杂志访谈还是小说前言,似乎对评论家的敌意进行敌意地反击才是他真正想干的事情。在《斩首之邀》的前言里,纳博科夫就如此写道:“我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我每出一本书,评论家们总是忙不迭地寻找多少有些名气的作家,以便进行充满热情的比较。”同时,他还揶揄了大家所喜欢的乔治·奥威尔。
在《庶出的标志》前言里,他又再度强调乔治·奥威尔是二流的陈词滥调式作家,并在再度提及评论家们总喜欢不动脑子地去讨论《斩首之邀》的“总体思想”之前如此声明:我不“真诚”,我不“挑衅”,我不“嘲讽”。我既不是“道德说教者”,也不是讽喻者。政治、经济、原子弹、原始而又抽象的艺术形式、整个东方世界、苏联俄国“解体”的迹象、人类的未来等等,令我极其无动于衷。

而谈论纳博科夫所带来的愉悦,则可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在自然之中找到了我在艺术中寻求的非功利的快乐。两者都是魔法的一种形式,两者都是一个奥妙的巫术与欺骗的游戏。”正如他对蝴蝶的着迷一样,他的小说文本总是充斥着各类琐碎无比的美丽细节和反复对照的文字迷宫。作为高度审美型的小说家,细节就是一切。所以,他才会不断反复地拒斥评论家们总是动辄给他的小说寻找中心思想,甚至认为这不仅是误读,更是对他的冒犯。
“好奇心是不服从的最纯粹形式”
《庶出的标志》是纳博科夫最具政治色彩的一部小说,从构想到成稿之间,纳博科夫既经历了纳粹德国的疯狂,也远观了苏俄帝国的膨胀,同时还体验了美国社会的自由,当然还夹杂着战争狂徒对薇拉和德米拉造成的人身威胁的焦虑。在 1940 年刚到美国的初期,纳博科夫就用希特勒和达·芬奇做对比,说出了他心中的文明观念:“从达·芬奇那里拿走他的自由、他的意大利、他的视力,他仍旧伟大;从希特勒那里拿走他的加农炮,他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狂热小册子的作者,一个无足轻重的家伙。”
而在《庶出的标志》这本小说中,纳博科夫正好建构了一个优雅的哲学家作为文明的象征,来抵抗全副武装而又荒谬可怕的极权领导。
小说故事可谓直截了当:曾被哲学家不断欺负的同班同学为了国家更加美好而发动政变篡权上位,通过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对内殖民的武装暴力来建构一个万众齐心的美好国度,而哲学家却因妻子去世和思想研究而对国家事务无动于衷,一颗纯粹的好奇心总铺在哲学思想领域,或者陷入妻子离世的悲切伤痛之中,以及对儿子安全的顽固焦虑之下。哪怕周围的朋友们一个个对领袖纷纷运动式表态,以及不服从的朋友们逐渐被失踪,哪怕亲眼见证过朋友在家中被包裹着优雅文明面孔的秘密警察从自己眼前带走,他依旧优雅地与接受国家任务改写《哈姆雷特》服从新政权意识形态的新剧本的剧作家一起谈论着莎士比亚的遣词造句,直到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后立马被故作优雅的秘密警察破门而入并带走,这位优雅的哲学家在被秘密警察以儿子安全为威胁的情况下才丧失优雅。
他被带走的理由,并非他是一个鲜明的自由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有学问却不为国家服务——注意,不是说他因不服从的反抗而犯罪,而是他因既不服从也不反抗所呈现的对国家缺乏兴趣而犯罪,暗示着人只能且必须对国家意识形态感兴趣而不能对其他感兴趣(当然,因为他对领袖不感兴趣反而让领袖对他感兴趣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从小说故事来看,《庶出的标志》可谓政治色彩极度浓郁,很容易归纳为奥威尔式的反乌托邦小说类型,但纳博科夫既瞧不起奥威尔的反极权小说,也不愿接受自己的小说被概述为政治类型的文本。单看书中充斥着极权色彩的人物,必定将小说看作是政治小说,然而纳博科夫自己在《前言》中特意声明,这些人物并非类型人物式的存在,也非某种思想的载体,他写的主题是“那颗充满爱意的心的跳动,是那种强烈的温柔的情感被挟持之后经历的折磨”。纳博科夫的言下之意,是要我们去注意一个个体在一个怪诞邪恶的人质国家里的个体意识,要我们去注意生活在极权国家里的独特个体的意识活动和永不停止的头脑思维是如何运转和随着时局而变化的——这就需要我们对小说细节的认真捕捉。
没错,细节。纳博科夫是书写细节的文字高手,以致于他对待细节的认真态度往往打断故事情节的叙述。在《文学艺术与常识》里,纳博科夫就说过:“我想像得出我的年轻的梦想家们,上千成万地浪迹在地球上,在肉体的危险、苦痛、尘雾、死亡、最黑暗却又最斑斓的岁月里,保持着同样非理性和神圣的标准。这些非理性标准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意味着细节优越于概括,是比整体更为生动的部分,是那种小东西,只有一个人凝视它,用友善的灵魂的点头招呼它,而他周围的人则被某种共同的刺激驱向别的共同的目标。”
《庶出的标志》的重点就在于对“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生活在极权高压下走钢丝的克鲁格夹杂于丧妻之痛和儿子安全的情感变化,在被极权领袖强迫为政权表忠心的死亡之途中,作为个体的克鲁格是如何一步步从优雅文明的典范变成歇斯底里的疯子的,个体意识是如何被集体运动所摧毁的。
然而,纳博科夫笔下的文明典范最终的结局,或许正如另一位来自俄国的作家布罗茨基所说的那样:“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越丰富,他的趣味越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越准确,他也就越自由,尽管他有可能越不幸。”尽管这位“文明的典范”在歇斯底里的抓狂下最终面临着鹰犬的子弹,但纳博科夫在残酷美学中安慰我们:“好奇心是不服从的最纯粹形式。”

纳博科夫画的蝴蝶手稿
在阅读这部看似政治色彩浓郁的小说之前,我们不妨对比一下纳博科夫与他父亲之间的反差:纳博科夫的父亲致力于社会性的自由主义实践活动,而纳博科夫本人则一再强调自己对现实事务毫无兴趣,不断声称小说创造去政治化,甚至在《文学讲稿》中坦言:“风格和结构才是一本小说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些空洞的废话。”
所以,在阅读《庶出的标志》时,我们应该去捕捉的是纳博科夫的语言风格和小说结构,而不要去捕捉小说的虚构背景是否在指涉某个国家的历史或某个时代的面貌:“我不相信‘历史”能够脱离历史学家而存在,如果我想选择一个档案保管人,我想还是选择自己比较安全(至少,出于我的心安)。”
纳博科夫不信任历史本身,因为历史会“经由平庸的作家和狭隘的评论家不断地修饰”。所以,纳博科夫用文学的想象力去虚构一场文字的盛宴,将历史当做梦而不是文献来对待,用艺术想象对个体精神的召唤力,对专制暴政进行沉重的打击。
极权意识形态是“精神食人主义”
在纳博科夫的这本小说中,不仅主人公克鲁格的个体意识有悖于极权领袖宣扬的集体式均等主义,连纳博科夫自己也与之较劲。作为篡权上台的极权领袖巴图克,组织的党派叫“普通人党”,暗示着他所统治的国家的每个人都应该普通得人人都只能拥抱埃克利斯主义这种机械化、平均化的人格与思想,甚至巴图克的父亲还发明了能够复制他人笔迹的打字机,他从这种机械装置中看到了统治的前景,那就是人格和笔迹一样是可以复制的,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应该像复制笔迹的打字机一样,如同二十五个字母一样“安全地”排列组合,一起朝着从吃喝拉撒到人格思想都平等的美好未来齐头并进。纳博科夫将极权领袖所信奉埃克利斯主义称之为“精神食人主义”。
然而,克鲁格作为文明典范的哲学家,总是被各种环境所造成的意象和丧妻的幻觉所诱惑,好奇心总是催生各类生活的想象,从幽会情侣披肩的晶片饰品联想到外太空的星系等,甚至还借助小说中给人以强行插入感的《哈姆雷特》改编情节,提醒这位总是充满好奇心的哲学家:“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里所没有梦想到的呢。”这位总是从现实环境中幽游于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哲学家,面对的却是一位恨不能删繁就简的极权领袖对他的“青睐”。
面对受雇于机械复制打字机灵感所催生的极权领袖,纳博科夫在改编《哈姆雷特》的细节叙述下,安排了克鲁格对哈姆雷特语言风格的不断推敲以及对语言翻译的不同对比,无论是推敲还是翻译,都意味着对机械复制化的“最简单”的语言的无意识反抗或者说自由意识无意之中对极权集体美学的反抗。
更有意思的是,善于文字游戏的纳博科夫,自己也与虚构的极权领袖做搏斗,对于小说中机械复制的语言,纳博科夫戏谑似的在小说中不断杂糅着法语、俄语、拉丁语、德语及纳博科夫自造的巴图克格勒语,借助自身对语言的操练能力不断地与之反抗——不仅小说主人公在反抗简化的语言和均等的思想,连纳博科夫自己也要加入这场个体意识对极权美学的战争之中去。
情节、韵律、意象、语言、双关语、回文、戏仿和暗语,这些纳博科夫生怕读者不知道,在前言中自己做出了长篇大论,最值得注意的是“双关语是一种文字瘟疫,是一种文字世界中的传染病”。
无论是双关还是回文,纳博科夫的炫技简直让读者感觉“惨无人道”,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名称乃至人与自身所构成的矛盾冲突,都形成了繁密而精致的迷宫:似乎每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的双关,每一个人名都是另一个人名的暗语,每一件事物都是另一件事物的回文,每一个情节都是另一个情节的戏仿……
比如纳博科夫说“哈姆莱特(Hamlet)”可以写作 Ham-let(火腿片),或者是法语 Homelette au Lard(肥肉片摊鸡蛋),而“Telemachos”又意指“来自远方的战斗”:“把这个词修剪修剪,拿掉不需要的字母,那些都是次要的补充,然后这个词就变成了'Telmah'。现在,你再倒过去读。这就是一支妙笔与一个胆大无耻的思想私奔的结果,而倒过来的哈姆莱特则成为了尤利西斯的儿子,杀死了他母亲的情人们。”
而极权领袖巴图克(Paduk)的名字发音近似俄语падать一词,意为“倒塌”,读起来又像英语单词paddock,在莎士比亚时代意为“蛤蟆”,而巴图克本人的绰号就是“蛤蟆”。然而,正是这位丑得如同癞蛤蟆一样的“蛤蟆”,却向往着一个整齐划一的“美好国度”。

如同癞蛤蟆般丑陋的“蛤蟆”意欲追求完全均等的“美好乌托邦国度”一样,纳博科夫在小说中不断地刻画着极权之下的各种冲突,乃至每个人本身内部的矛盾,如同宣告着极权所追求的“完美化”是绝对不可能的存在。
在那个警察国家,秘密警察去粗鲁地逮捕自由主义思想者时,却穿着极度绅士的西服前往;这位灭绝人性的秘密警察带着穿着优雅的情妇一同前往,在逮捕过程中却互相调起情来,如同一场充满温情的优雅绅士的逮捕行动。而克鲁格在一座完美对称的桥上路过时,负责查验证件的士兵却是个不识字的文盲,以致于克鲁格差点过不了桥,待得他拿到士兵想要的能够证明他能够过桥的证据时,克鲁格返回桥上时却又发现守卫的士兵早就擅自离岗,白忙活的克鲁格其实根本就不用回去拿证据——这座阻挡国民自由的桥梁“没有了阻挡”。
在讲究最简单最直接最正确的信息传播的国度,暴政的拥护者却错误地执行了针对克鲁格的人质行动,以致于纳博科夫的小说提前进入了尾声,而巴图克的愿望也随之落空……
爱是“庶出的标志”的最佳象征
当然,整部小说最重要的是克鲁格在这个人质国家中被领袖“青睐”之后,他个人情感面对均等美学的逐步变化。
无论作为文明典范的哲学家,还是作为抓狂发疯的人质;无论亲朋好友逐步被失踪而自己尚且处于安全的生活之中,还是最终因儿子被当做人质而被强迫拥抱极权思想导致的歇斯底里,纳博科夫从头到尾都安排着小说开头就被宣告死亡的妻子奥尔嘉时刻现身,幽灵似的充斥着克鲁格整个情感变化之中,还有丧妻后他极力保护的儿子大卫也不断出场,对妻子的思念和对儿子的护卫构成了克鲁格情感变化的最本质线索,而非荒谬邪恶的极权社会对他造成的政治压迫。
纳博科夫想要让我们体会到,“死去的妻子和正在熟睡的孩子”所催生的爱,是对极权反抗的最本质行动。因为,爱是“庶出的标志”的最佳象征,“精神食人主义”无论如何疯狂与邪恶,都无法阻止个体的爱,尽管极权能够摧毁我们的所爱……

然而,极权之所以能够借助暴力摧毁我们所爱的人、事、物,也正是因为极权能够挟持“我们的爱”,在挟持“我们的爱”来改造国民的同时,却无法真正摧毁“爱”本身,也就有了小说中克鲁格癫狂地复仇之举,尽管即将死于枪弹之时(注意:纳博科夫并没有安排他的死亡,子弹即将进入身体之时小说就结束了,而纳博科夫作为导演身份掐断了后续并自己出场了),但纳博科夫却安排了这样一个场景:巴图克及其鹰犬一步步逼他终于踏入死亡的临界点时,克鲁格反而坠入了与妻子、儿子相见的温暖梦境中——在巴图克和他的走狗们发出咯咯笑声的时候,克鲁格“沉入到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温柔之中,沉入进一种迟到的让人头晕目眩的深深的永恒的爱抚之中”。
在子弹射入克鲁格身体的一瞬间,纳博科夫自己出场了——纳博科夫伸展着身子从杂乱的稿纸里抽身出来,从窗户上看着暗夜里对面的窗户:“一个不错的飞蛾扑火的夜晚。”
原来,整本小说的漫长日夜不过是纳博科夫想象的一个夜晚。
在这个温暖湿润的夜晚,纳博科夫面对稿纸的想象驰骋与克鲁格的时空漫游形成了对照,也如纳博科夫在暗夜里看到的那个精致的水坑一样,与克鲁格在生命不同阶段不断看到的水坑形成了对照,模糊了小说与生活、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于是纳博科夫起身宣称:“我赋予那个可怜人的不朽是一种含糊的诡辩而已,一种文字游戏。”因为,身处时空中的我们终究都得死去,人之死亡不过是“一个节奏的问题”,而我们每个人的死亡风格却可以由我们自己去定义,那么我们生前又该如何度过我们一生的节奏呢?
(完)
本文原发于公众号
单读
id:dandureading
刊发已获授权,在此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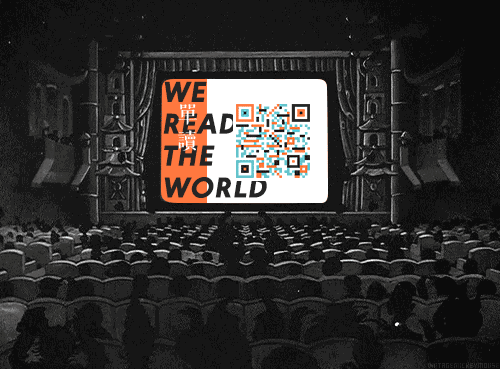
长按上图二维码可添加关注
相关图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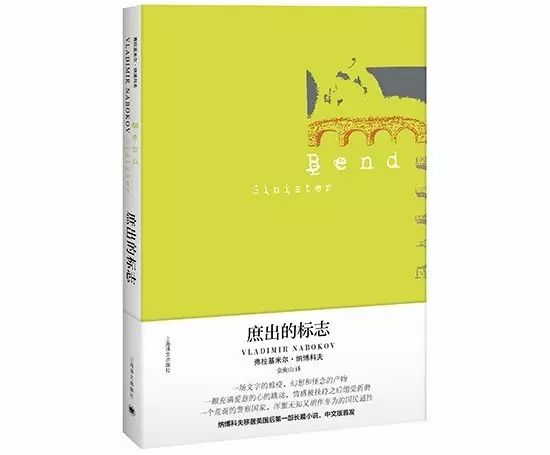
《庶出的标志》
(纳博科夫作品系列)
[美]纳博科夫|著
金衡山|译
《庶出的标志》是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后第一部长篇小说,将现实的见闻与经历编织进虚构的文字之中,集政治讽喻、人物肖像、文字游戏于一体,穿插对文学经典的颠覆解读。小说的背景置于一个荒诞不经的警察国家,人们信奉埃克利斯主义,追求整齐划一的埃特盟(普通人)式生活,浑噩无知又胡作非为是国民的通性。
必须要去书店买走的两本重磅好书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
逢珍|译
文学大师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作品在国内首次完整结集。68 则风格各异的短篇小说,由纳博科夫之子德米特里按照年代顺序编辑而成。
夜晚书桌前的男人被一位不速之客惊扰,原来是来自故乡的木精灵;失散已久的儿子与母亲重逢,却现身在无比尴尬的时刻;羞涩的梦想家与恶魔做了灵魂的交易……
在这些幽暗而充满魔力的故事中,纳博科夫完美展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小说技法,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智力游戏,以及对生命中无从躲避的暧昧和失落的迷人洞察,被称为“英语文学的奇迹”。
点击封面可看详细
《刺杀骑士团长》
第一部显形理念篇
第二部流变隐喻篇
[日] 村上春树|著
林少华|译
村上春树时隔七年长篇巨著
关于创伤、内省、对峙、重生的力量之作
2017 年度日本小说类榜首
一幅藏匿于阁楼的惊世画作串起二战创伤与现实吊诡
童年的痛失、家庭的破碎、战争的创伤
夜半铃声和古庙洞穴
不请自来的骑士团长……
面对无法挽回的失去,
他告诉我们,
回到洞中。
直面无以名之的恶。
点击红色粗体字看详细
长按下图二维码可至预售页面

三月全面上市
敬请期待

上海译文
文学|社科|学术
名家|名作|名译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
或搜索ID“stphbooks”添加关注


